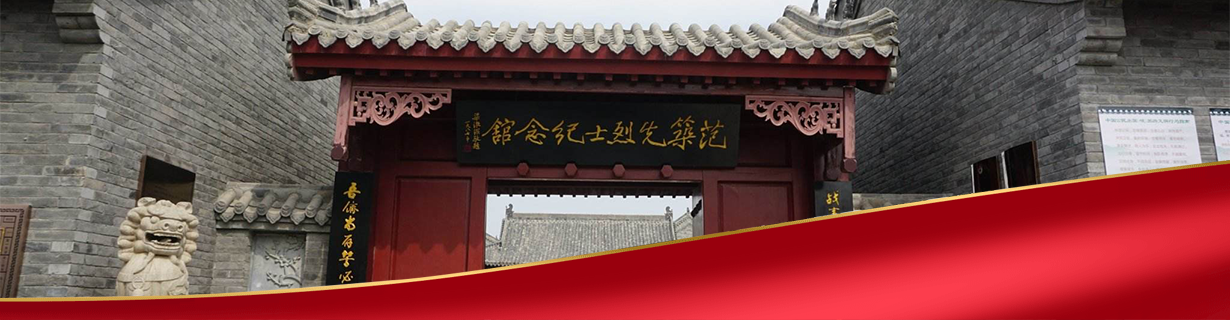
聊城老区网
2012/08/29 浏览量:
周金凤 韩兆星
革命历史小说《红岩》上个世纪60年代初出版后,大家争相购买、先读为快,已发行近400万册。小说《红岩》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使他们树立起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树立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如今,又成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一部好教材。
1991年10月,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举办的《红岩魂》展览在广州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开幕式结束后,与展览中心同处一幢大楼的广州中央酒店的老总带着西装革履的部门经理们,恭恭敬敬地把一位出席开幕式的衣着十分简朴的老者迎进了酒店的贵宾室,老者却并无拘束之感,侃侃谈起他那传奇的人生经历。
这位老者,就是《红岩》书中主人公之一华子良的生活原型,阳谷县石佛镇韩庄人韩子栋。
韩子栋(1908—1992)原名韩国桢,生于1908年一个农民家庭里。早年读书,青年时到淄博鲁大煤矿当矿工,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932年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参加工人罢工斗争,受到反动当局的通缉。面对反革命的屠刀,韩子栋同志革命信念更加坚定,同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韩子栋受党组织的委派,设法打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内部。他在北平(今北京)开了个书店作掩护,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以非凡的智慧和胆略,组织起党的地下情报网,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1934年由于叛徒出卖,韩子栋身份暴露,在北平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逮捕。1935年,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何梅协定”,国民党势力从华北向南方撤退时,韩子栋即从北平押回南京。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又被押解上路,先后在汉口,益阳等地被关押。
直到到达贵州省的息烽集中营,和罗世文、黄显声、宋绮云、许晓轩等相识以后,韩子栋才从多年孤军奋斗、与世隔绝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他曾与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多次商议集体暴动越狱计划。抗战结束时,还曾设法将这暴动计划送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报告提出:息烽集中营战友被敌人转押重庆途中,寻求机会,在川黔险峻的山间公路上暴动越狱,希望党派出游击队武装予以接应。送信的同志冒着危险,早将信送到了,而且还冒险将结果告诉了狱中的同志。但却一直等不到党组织的回信。
后来,息烽集中营被囚同志被集体押往重庆时他们又想到了这事,并曾设想在川黔途中伺机行事。但终因未寻到适当机会,而错过了在川黔的山间公路上可能暴动脱险的机会。
1947年8月18日罗世文、车耀先二同志牺牲后,敌特对集中营的控制更加严密。许晓轩同志决策:韩子栋早已用神智不清的方式麻痹了敌人,借以联络狱友,组织对敌斗争。给敌人造成错觉,趁敌特还让他到瓷器口河街挑菜的机会,就应坚决出去!现在不应该光想集体越狱,只要有可能,“走出一个,是一个!”
1947年8月16日狱中党组织通知韩子栋在适当时机越狱,8月18日这一天,韩子栋又被敌特押去靠近集中营的一个市场——瓷器口河街买菜。这市场就在嘉陵江边,押解他的特务要在街上找地方赌钱,就叫他单独去河街挑菜。韩子栋看见特务果真走进了一家菜馆去了,一折身,甩了菜担子,就上了停泊在江边的渡船。他把身上的钱全给了船工,船工也就不再等别的乘客,立刻将渡船划过了嘉陵江。
为了避免狼犬追踪。过江以后,韩子栋换了一双新鞋,就一直向前闯去。
为了避免在途中可能留下什么痕迹,他决计不向任何人问路,也不向任何人寻觅食物。饿了,就从乡下还没收净的红苕地里找红苕吃。找的多的时候,就带上几个红苕赶路。
一路上,只有两件事使他感到困难。一件是乡下养的狗多,沿途就追着陌生人乱咬。打狗么,怕惊动别人,他只好不理它一直往前走;即使被狗咬了两口,也不理它。另一件事,是对四川的地理环境不太熟悉,由此给他带来许多麻烦。韩子栋记得清楚极了:天上的北斗星就是前方,他看准了,才从阴森森的古墓里爬出来的,他决不曾离开过已经看准的方向。他也决不曾因为野狗的疯狂追咬而离开过。可是,第一次,他便惊讶的发现:他走了一夜,那弯弯曲曲,绕来绕去的山路,竟又将他带回开始出发的地方来!他今晨钻进去的古墓,还是他昨天白天藏身的那座古墓!
他只得改变办法。从此他不再顺着路走,只要看准了北斗星的方向就一直往前;逢山翻山,遇水涉水,决不转弯,一直向北方闯去。
他就这样,一直走了三个半月,才走出了四川地界,从河南进入解放区。他看见到处都写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标语,他听见到处都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他才从枯黄的青纱帐里走出来。
“你是什么人?”
韩子栋望了望出现在他身边的民兵弟兄,一时间激动的不知说什么好。他瞬间真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是,他想着狱中的同志要他向中共中央汇报的委托,他向盘查的民兵弟兄,以及县委、地委的同志,就只会说一句话:“我找周恩来!”
就这样,他终于找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回到了党的怀抱。
此后,韩子栋被派往冀鲁豫区参加土改工作,再次投身到革命的浪潮之中。
建国初,韩子栋先后担任中财委人事局科长、北京机械厂副厂长、国家人事部副处长、国家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科委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58年调贵州省工作,此后历任贵阳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监委书记、省政协副秘书长、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当选为政协贵州省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韩子栋曾受到极左路线的冲击,他同“四人帮”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85年离休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关心下一代和青少年教育事业中去。他经常往返奔波于全国各地,以自己特殊的斗争经历,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同时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调研中,韩子栋发现当时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与青少年道德品质教育的滞后形成强烈反差。他担心这样长期下去,会导致青少年的精神滑坡,这使他产生了用“小萝卜头”的形象和精神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想法。
1990年,韩子栋受中国关工委和中国优生优育协会的委托,组织一些老同志筹办了“小萝卜头少年教育委员会”。在给青少年作报告时,他多次深情地回忆了“小萝卜头”这位在狱中与他共同传递情报的“老战友”。为了让“小萝卜头”的生动形象扎根于孩子们心间,韩子栋倡议为“小萝卜头”塑像。在“小萝卜头”的哥哥宋振镛等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北京、上海、西安、江苏、河北、重庆、贵阳等地的少年儿童活动场所,均树立起了“小萝卜头”的塑像。每年都会有大批少年儿童来到这些塑像前,缅怀先烈,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不少中小学都开展了“向‘小萝卜头’学习,做党的好孩子”的活动。
1991年,韩子栋的肝癌已经到了晚期,但躺在病榻上的他,心中想的仍然是关心和教育下一代。他在逝世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要争取活到90岁,还要再干几年,在全国多塑些‘小萝卜头’像,为教育青少年再多做一些工作。”
1992年5月逝世于贵阳,享年84岁。1989年秋,韩子栋探家期间,分别在聊城地区行署礼堂和阳谷县电影院给广大干部群众作过生动的报告,听报告的人们至今记得韩子栋的传奇人生与革命历史小说《红岩》中的华子良有不少相似之处,华子良这一闪光的英雄人物永远活在人民心中,韩子栋的美名,也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